PG电子官网- PG电子试玩- APP下载城中村题材纪录片:用看见完成一场反边缘化抗争
2026-01-28PG电子,PG电子官方网站,PG电子试玩,PG电子APP下载,pg电子游戏,pg电子外挂,pg游戏,pg电子游戏,pg游戏官网,PG模拟器,麻将胡了,pg电子平台,百家乐,捕鱼,电子捕鱼,麻将胡了2在近期揭晓的第十五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获奖名单中,最佳大学生纪录片奖《大厂四栋》和最佳纪录电影奖《胡阿姨的花园》都将镜头聚焦了城市空间中的边缘地带:城中村。现代城市快速发展,却暂时将一些角落遗忘,形成城中村。这里往往集聚着外来务工人员、残障人士、老年原住民、无业游民等多元社会群体,因而暴露出住房、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


如何看见呢?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三重空间叙事理论提供了一种路径。三重空间即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及精神空间。列斐伏尔指出,可以将创作文本与其背后聚焦的空间形态紧密相连,使文本内容更好地浓缩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并赋予其形态理念和价值内涵。那么,优秀的城中村题材纪录片是如何透过三重空间的棱镜,达成一场真切、平等而立体的看见?

物理空间即故事发生的场所,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所推崇的长镜头与景深镜头,是城中村纪录片呈现物理空间的常用方式。
面对城中村错综的空间,跟随人物行走的长镜头成为展现空间全貌的重要拍摄手法。在《大厂四栋》中,当郑江红在麻将馆被打后转身离去,镜头便跟随他一瘸一拐的身影,从拥挤的麻将馆进入大厂村的窄巷,自然呈现出坑洼的路面、破损的墙体、地上的垃圾、随意停放的车辆等以拥挤、凌乱为特征的物理空间。在《胡阿姨的花园》中,胡阿姨行走是贯穿始终的动作——镜头长时间陪伴她佝偻着腰,穿行在低矮的棚户区、狭小昏暗的旅店、逼仄的公租房、拾荒的街巷以及她建造的花园等多个物理空间,让观众既能沉浸式地感受胡阿姨的生活空间,又能在时间的绵延与空间的反复中,见证她与空间的相互塑造。


与此同时,聚焦单一空间的景深镜头,则通过画面纵深层次的建构,完成对空间细节的犀利刻画。在《厚街》中,厚街4423号房屋是没有屋顶的,当摄影机从上方一家家掠过时,每一个格子间中都是狭窄的床铺、高低错落堆放的杂物和拥挤的租客,将居住空间毫无隐私且简陋逼仄的特点暴露无遗;《大厂四栋》在拍摄麻将馆争端的时候,使用了短焦镜头近距离记录:前景是餐桌、中景是打架的人、背景则挤满了围观和劝架的人——所有元素被全部压缩进同一空间,精准呈现出麻将馆这一社交空间的拥挤与混乱;在拍摄叶源伟的按摩店时,则使用了长焦镜头远距离观察:玻璃门前是明亮而喧嚣的街道,玻璃门后,叶源伟独自在按摩店中——按摩店近乎要隐匿于昏暗之中——他赖以生存的工作空间只是城市中一个不被看见的角落。
“三重空间”中,物理空间是物质载体,也是其他空间得以存在的基础。城中村题材纪录片充分利用长镜头与景深镜头,让观众既见城中村的整体构造,又见其微观细节,从而实现对物理空间的立体化呈现,为深入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提供了现实依托与沉浸式体验的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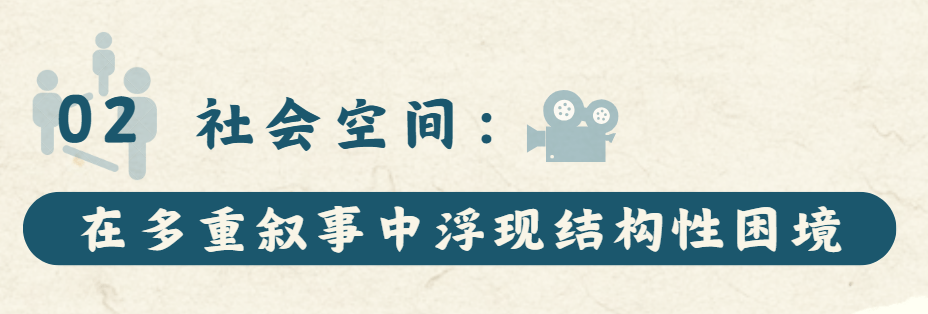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不仅是物理的或自然的存在,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和载体。城中村集聚着多元社会边缘群体,交织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潜藏着众多尖锐的社会问题。纪录片深入这片空间,通过多重叙事方式,让结构性困境在一个个真实而具体的故事中逐一浮现。
部分城中村纪录片选择锚定一个具体的人物,通过长达数年的跟拍记录其生活的流变。而当我们穿透流变的表象,不变的困境便浮现而出。《二十四号大街》就是如此。导演潘志琪跟拍老苏7年,记录了他从在二十四大街经营无证餐馆,到餐馆被政府拆除决定回家,再到发现家人不接纳自己而再度漂泊,最终到他在土坡上放了一张床、搭起四面架子,建立了新的“家”的全过程——老苏的生活一直在变化,但“容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的悬浮处境未曾改变,而这也正是以老苏为代表的进城务工者共同的社会困境。

另一部分作品则选择通过记录群像,呈现一个完整的城中村社会切面。在这个切面中悲喜是交织且点到即止的:悲剧发生后,个体的后续常被留白,然后被新的故事覆盖;此时欢愉的个体,未来可能经历悲剧,这让影片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而造成不确定性的原因恰恰是人物普遍承受的社会结构性困境。《风起前的蒲公英》记录了多个孩子离开合唱团的经历,而这些带着刺痛的离开常穿插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比如张展豪因为考学限制放弃唱歌的梦想并离开学校,紧跟的是孩子们各自欢快的假期生活;权煜飞因变声被要求离开合唱团,紧跟的是全女合唱团参加公益演出......创伤是真实的,但生活必须继续。在一次次突然地离开中,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与不充分,这一造成创伤的重要原因,得以反复确认与强化。再如《厚街》中,新生命的诞生、恋爱、团聚的“喜”与分手、煤气罐爆炸、激烈争吵、讨债砍人、为钱卖淫的“悲”也交织在一起。影片在故事的大起大落中直指问题根源:911事件导致的裁员潮,让生存,成为外来民工每天挣扎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钱、没有社会保障、没有人把这里当成真正的家,稳定的生活自然无从谈起。

除了聚焦城中村空间内的生活,镜头常跟随人物进入城中村外的空间,在对比叙事中,让隐形的社会阶层壁垒无所遁形:当《风起前的蒲公英》中的孩子们为上流阶级的慈善晚会表演时;当他们明明不属于北京却要演唱《北京欢迎你》,用心排练后却被要求假唱时;当胡阿姨瘦小佝偻的身影穿梭在商场、解放碑广场等城市现代化设施空间中,其背着背篓行走的匆匆与周围人群的悠闲形成鲜明对比时;当《大厂四栋》中盲人刘铁成去公园拉二胡卖艺谋生,却在警笛响起后立即停止演奏时……这些时刻无一不强化着他们是城市中格格不入的“他者”的事实,而那道让其成为“他者”的阶层壁垒,正是城中村的困境持续存在的结构性根源。
至此,城中村纪录片通过个体、群像与对比的三重叙事方式,完成了对社会空间的立体化呈现,让我们真正看见了流动的背后那固化的多重结构性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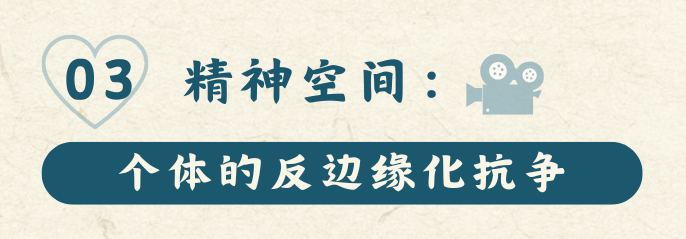
精神空间即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果说城中村纪录片中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揭示了边缘化的现状及成因,那么精神空间则记录了个体的反边缘化抗争。
抗争首先源于个体的自尊与自爱。在《风起前的蒲公英中》中,权煜飞的那句“每个人都是一个好苗子,有的栽在了黑土地里,有的栽在了红土地里,有的栽在了沙漠里”,是在看清“土壤”局限后,依然肯定自己作为“好苗子”的个体价值。在《大厂四栋》中,脚部残疾的郑江红多次向镜头宣告自己不比健全人差:他坦然脱鞋展示缺陷,随即以俯卧撑和打拳骄傲地证明自己的强壮;他不断强调自己朋友多、什么都不怕等,都是他对“残既弱”的社会偏见的反抗。

抗争是对自身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创造。在失序混乱的厚街,依然有人不愿意向命运低头,喊出“我不想种地,我不服气,我还是想打工,我要流浪一辈子”;《大厂四栋》中左眼失明、右眼高度近视的叶源伟会骑电动车去地铁口接妻子,会弹吉他唱情歌,努力创造着生活中的幸福与浪漫;胡阿姨更是将这种创造推向极致:在最破败的十八梯,用拾荒来的废品建造了一座五彩缤纷的花园,创造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诗意空间。
抗争更是向外释放温暖。郑江红看到醉汉的三轮车倒地无人扶助,立刻一瘸一拐地去帮忙,虽然因为身体的缺陷,他一个人根本扶不起来,但他依然要帮,从天亮一直帮到天黑;当他的朋友老陈肺癌晚期被子女遗弃,他主动陪床送终。胡阿姨连吞药片的水都不舍得买,却默许他人拖欠房费,还借钱给更困顿的房客。这些城中村里的生存者与建设者,用行动证明了即使在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双重挤压下,人性的良善仍然可以熠熠生辉。

从对内的自尊自爱、努力生活,到对外不求回报地释放善意,纪录片通过看见个体的精神空间,确证了人之为人的主体性,无法被任何结构性困境所轻易剥夺:城中村的他们不再是被同情甚至被俯视的弱者,更不是刻板印象中素质低下的混混,而是有能力建构人生意义、值得被尊重的生命主体。
导演周浩在《厚街》中说:“通过这个片子去改变所有民工的命运,我觉得是一个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事情,但这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镜头里那个失序混乱的厚街已不复存在,而每一场改变永远始于看见。通过镜头我们走进那些真实的生活空间,看清了交错的社会结构性困境,感动于那些即使身处困境仍用力生活、回馈世界善意的个体——从这场真切、平等、立体的看见开始,我们已然和城中村的他们站在了一起,共同开启了一场始于影像、但终将归于现实的反边缘化的抗争。
[1] 许继华. 城中村题材纪录片中的影像表达与“生活流”叙事--以毕业作品《大厂四栋》为例[D]. 云南艺术学院,2025.


